最初开始读《白》,一来是因为它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身份,二来是逆反心理作祟——越是什么被贴上“露骨”、“禁书”的标签,越是对什么谈之色变,我就越想去了解它、去亲近它。
果不其然,又被我遇上一部佳作,甚至可以称为一部史诗。小说洋洋洒洒五十来万字,用极具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叙述了“白鹿原”这片虚构的秦地高原上“白”“鹿”两姓家族的百年历史。虽地名是虚构的,但这方土地上发生的故事确是作者翻阅无数资料,前往各地走访、调查,再加以扬弃、润色得来的。“这种心理是我构思这部长篇小说时越来越直接的一种感受,一个正在构思中的类型人物,要有一个真实的生活里的人物为依托,哪怕这个生活人物的事迹基本不用,或无用,但需要他或她的一句话,一句凝结着精神和心理气氛的话,或独秉的一种行为动作,我写这个人物就有把握了。”
有人夸道:《白》的伟大之处在于它的深度和真实性。我想“真实性”这三个字用在一部魔幻现实主义著作上更显珍贵。一部好的魔幻现实主义著作给人的感受不能是生硬的、飘在空中的,而应该做到让你沉醉在这本书构建的世界中,分不清也不必分清真实与虚幻;要做到将一段古老的传说或村民口耳相传荒诞不经的故事揉进你的耳蜗里,揉进你沉睡的记忆里,让你觉得它真实存在过,在某个遥远的时间空间里。此外,我认为《白》的伟大之处还应再加一点:冷静的第三人称角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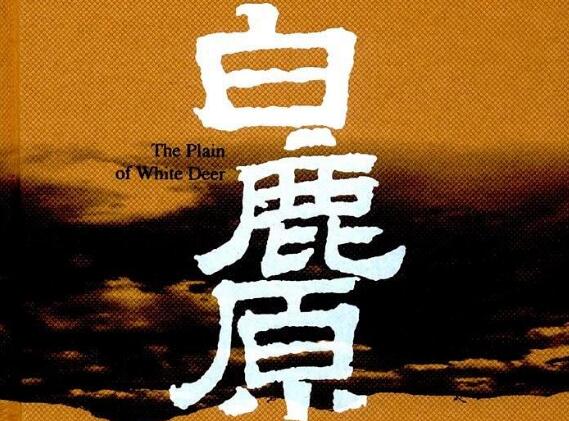
小说选取的时间是中国社会最为最为动荡的那百来年。从清政府腐朽的末年到新中国的成立乃至红卫兵、破四旧的出现,这些原本在高中历史教科书上冷冰冰的史实,却在小说微小的切入口下鲜活起来。百年的动荡凝练成一方土地上一个个鲜活生命的故事。哪怕是政治意味如此浓厚的选题,作者的叙事也不带偏向性。两党合作时的热烈、斗争时的激烈、双方的可贵之处、残酷之处都如实展现。就像鹿家的兆海和白家的灵灵,两人永远处于不同的党派,却也永远珍重彼此,也都分别为自己信仰的党派壮烈牺牲。
这样的客观性还体现在人物的描写上。读到某些篇章,你可能恨透了某个人物,但突然笔者话锋一转,将更细微的视角投注于该角色,你又顿生同情之心;或者相反,一个本是如此受人敬重的角色,也完全有可能下一章就沦落不堪。正是这样忠实的文风使得作者笔下的人物各个栩栩如生、饱满深刻。
小说最让我惊艳的一处是田小娥尿到鹿子霖脸上那一段。在此之前,小说处处充斥着男尊女卑、女性天生该为丈夫、公婆端屎端尿、女性天生就是生育的机器、传宗接代的工具等等这般论调。我甚至快以为这就是作者所秉持的信条。这时,田小娥出现了。
本是一位本分的老秀才之女,嫁给一位财东作二房,却遵循自己的欲望而活,和财东家的长工黑娃私奔到了白鹿原。这段恋情让黑娃父亲蒙羞,二人无奈离家,在原上的一处破窑洞里定居下来,生活清贫却甜蜜。但这样的关系是为社会所不忍的,女人们辱骂小娥的同时感到自身的高贵与道德,男人们羞辱她的同时渴望得到她。读后感www.simayi.net后来因为变故,黑娃出逃,小娥为了在乱世中保护丈夫保护自己,用身体和地头蛇鹿子霖鹿乡约做交易。而鹿子霖为了羞辱一直强过自己的族长一家,设计让小娥色诱族长的长子致使其堕落。小娥与族长一家本也有过节,但计谋成功后她并没有复仇的快感,满是自责与懊恼。而鹿子霖却怀着小人得志的自豪来向小娥求欢,就这样,发生了这一幕:
鹿子霖正陶醉在欢愉之中,感到脸上一阵湿热,小娥把尿尿到他脸上了。鹿子霖翻身坐起,一巴掌扇到小娥脸上:“婊子!你……”小娥问:“你刚才不是说了今黑由我想咋样就咋样……”鹿子霖恼羞成怒:“给你个笑脸你就忘了自个姓啥为老几了?给你根麦草你就当拐棍拄哩!婊子!跟我说话弄事看向着!我跟你不在一杆秤杆儿上排着!”小娥跳起来:“你在佛爷殿里供着我在土地堂里蜷着;你在天上飞着我在涝池青泥里头钻着;你在保障所人五人六我在烂窑里开婊子店窑子院!你是佛爷你是天神你是人五人六的乡约,你钻到我婊子窑里来做啥?你日屄逛窑子还想成神成佛?你厉害咱俩现在就这么光溜溜到白鹿镇街道上走一回,看看人唾我还是唾你?”鹿子霖慌忙穿起衣裤连连禁斥着:“你疯了你疯咧!你再喊我杀了你!”却不见小娥收敛,就慌匆匆跳下炕来夺门出窑。小娥在窑门口跟踪骂着:“鹿乡约你记着我也记着,我尿到你脸上咧,我给乡约尿下一脸!”
我在当时的男权社会中欣喜地看到了女性单薄却有力的控诉,这是小娥一个人向社会的宣战。
而对于那些恪守妇道、相夫教子的女性,作者在本书的后记中这样写道:这些女人用她们活泼的生命,坚守着道德规章里专门给她们设置的“志”和“节”的条律,曾经经历过怎样漫长的残酷的煎熬,才换取了在县志上几厘米长的位置。
感谢陈忠实先生为我们带来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作者:衠儿


发表评论:
◎欢迎参与讨论,请在这里发表您的看法、交流您的观点。